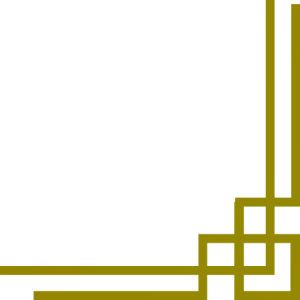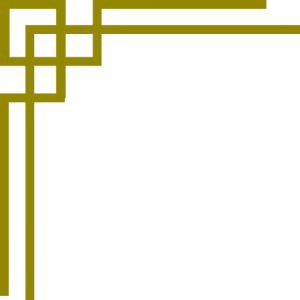


建设与领导革新工作
雪华堂成立之后,内部因派系问题引发争议。
因财务问题引发用地地契一度被政府收回,
吉隆坡永春会馆的黄重吉和洪进聪在最困难的时期挑起劝募大任。
1970年代永春人李延年与邱祥炽先后领导雪华堂,
引领雪华堂走向革新之路。
在最困难的时期挑起劝募大任
1923年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现已更名为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以下简称“雪华堂”)诞生之前,吉隆坡已成立了以下会馆组织:
一个业缘性会馆: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工商总会。
四个方言群组织: 福建会馆、广西会馆、海南会馆及潮州八邑会馆。
八个地缘性会馆: 赤溪公馆、茶阳(大埔)会馆、广肇会馆、东安会馆、福州会馆、会宁公会及嘉应会馆。
两个拟血缘宗亲会馆:吉隆坡暨雪兰莪叶氏宗祠、吉隆坡陈氏书院。
上述十五个会馆组织当中,其中五个是客籍人士所成立,一方面显示了客籍人士的势力强大,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客家社群的不团结。福建人、广西人、海南人,以及潮州人因为人口相对较少,也因此更感受到集结同乡来捍卫社群权益的迫切性。
建立雪兰莪中华大会堂这一个雪兰莪华人最高总机构的想法于1910年代已被提出,并经陆佑、张郁才、朱嘉炳等大矿家的倡议下,陆佑率先认捐五万元,同时获得当时的甲必丹叶观盛向政府申请一块地段。1923年8月23日,在朱嘉炳、张郁才、刘良颜及陆运怀的号召下,雪兰莪矿务总局和雪兰莪中华总商会联合其他社团和乡会代表在雪兰莪矿务总局召开华侨大会,才催生了雪兰莪和吉隆坡华社横跨业缘、方言及地缘纽带的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
雪华堂成立之后,拖延了十二年建筑物才落成。主因是对建筑物礼堂的命名为中山堂或陆佑堂而引发争执。1923年8月23日第一次华侨大会因感念陆佑先生对成立雪华堂的功劳,议决在雪华堂建筑落成后,选定一个适当场所命名为陆佑堂,并且为他铸造一座半身铜像安置在雪华堂内。然而,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逝世后,1928年9月1日,由叶宝清先生主持的第二次华侨大会,接纳了“雪兰莪华侨追悼孙公大会”的建议,以孙先生领导革命、推翻满清,肇造共和的巨大贡献为由,一致通过将大礼堂订名为“中山堂”。2自此,引爆了雪华堂建筑的大礼堂要命名为“陆佑堂”或“中山堂”的争议。也因此波及雪华堂建筑经费的筹募进度。甚至因内部派系之间的纠纷引发董事辞职,导致建馆进度被拖延,结果引发用地地契一度被政府收回。3
雪华堂创设阶段,永春人虽然不是领导核心成员,但一直都在协助雪华堂的组织工作。在第二次华侨大会推举的二十五人募捐委员团,在短短三个月内两位委员长先后辞职,吉隆坡永春会馆的黄重吉和洪进聪在这最困难的时期,挑起劝募大任,先后领导募捐委员团。4
雪华堂与吉隆坡永春会馆成立时间仅相隔一年(永春会馆成立于1924年9月27日),两个社团成立后即投入建馆工作,而雪华堂迟至1934年才竣工。反观吉隆坡永春会馆建馆工程与雪兰莪福建会馆的重建工作则分别在1930年及1932年已经竣工。这显示跨籍贯的社团组织整合的困难,远在地缘性社群与方言群组织之上。在这时期的吉隆坡永春会馆的部份领导人,同时也开始参与雪兰莪福建会馆和雪华堂的会务活动。其中黄重吉、洪进聪、颜滂沽和陈仁堧在这三个组织均居要职。在1935年雪华堂选出的董事会当中,黄重吉担任副总理(即现在的副会长职),陈仁堧出任常务董事。之后由雪华堂发动的许多活动,诸如二战时期成立“雪兰莪华侨援英义捐委员会”名单中的六十三人成员里,永春人也占了九位。5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建立初期一波三折
资料来源: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提供

黄重吉领导募捐委员团
资料来源: 吉隆坡永春会馆提供

黄重吉领导募捐委员团
资料来源:吉隆坡永春会馆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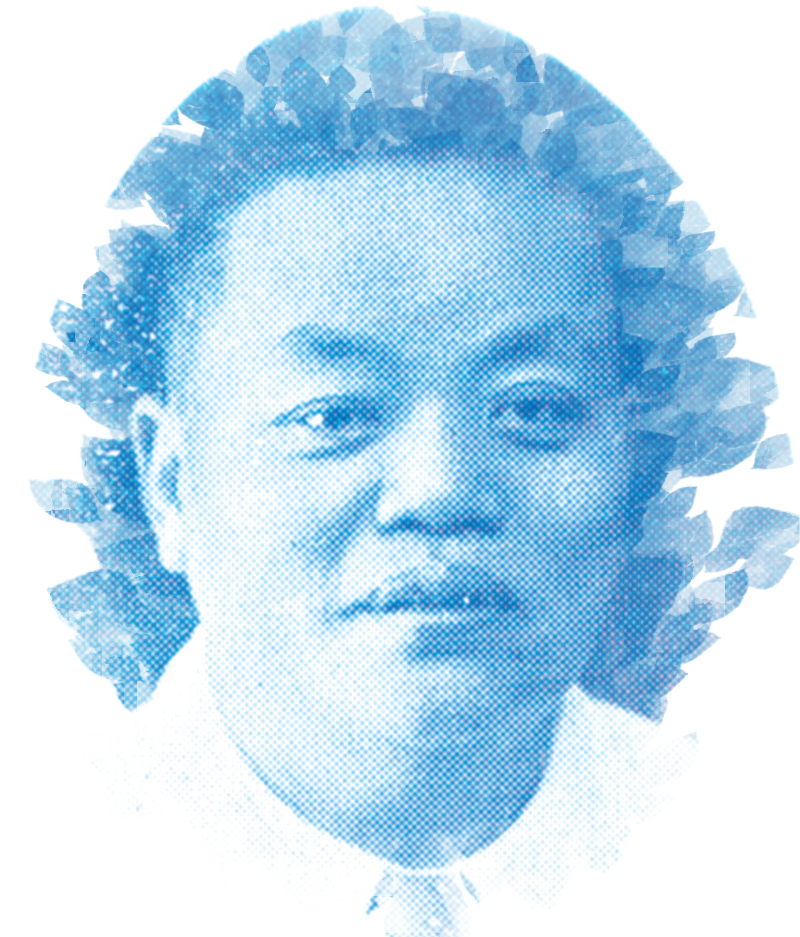
1970年代,永春人在雪华堂的影响力达到高峰。李延年于1963年已开始出任雪华堂副会长,1975至1982年更出任总会长一职。李延年的继任者邱祥炽亦来自吉隆坡永春会馆。在李延年担任会长期间,黄茂桐、郑棣等永春同乡人也在雪华堂担任财政要职。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永春乡贤同时在不同社团居要职,展现了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执事关联”特点。6这显示华人社会的网络建构,即是建立在同一批人于不同团体担任领导职务之重叠性的基础上。
李延年担任雪华堂会长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开放门户广召会员,激活了大会堂的生命力。在他就任雪华堂会长的一个月后,就着手进行改革,朝向雪兰莪州华人社团大团结的方向迈进。1975年6月24日,雪华堂董事会通过修改章程与申请成为非营利机构的议案。自此,所有雪兰莪境内华裔团体均可加入成为大会堂的会员。
1981年,雪华堂的会员从原有的22个单位激增到197个单位。7这个举措解决了雪华堂自创会以来会员数量单薄,在守业面对挑战的困难。
另外,在广召会员的同时,因开放让不同性质的团体加入,扩大了雪华堂的社会基础,这点除了激发雪华堂的活力,同时也提升了雪华堂社会的影响力。这段期间,雪华堂成立了许多委员会,并且吸纳了许多专才加入参与活动。李延年领导大会堂期间,黄茂桐、邱祥炽,以及周瑞标几位永春同乡也进入雪华堂董事会共同推动会务。
李延年领导时期,对于官方政策的不足之处,总是勇于公开批评,因而奠定了雪华堂成为勇于批判政策缺失的风格。追根究底,雪华堂能够在二十一世纪成功转型为“扎根华社、迈向多元”的公民团体,李延年上任后的上述改革措施功不可没。
李延年领导时期,雪华堂与华社的网络被构筑得更深、更广,这让李延年的继任者邱祥炽更顺利地去推动会务。祖籍永春县马洋的邱祥炽出任会长之前,曾出任文教主任一职,任内将雪华堂的文教活动办得有声有色。其中1977年出版了六十万字的雪华堂成立以来第一本纪念特刊。1983年4月至11月这段时间,雪华堂举办与推动了多项文教活动,8突出了雪华堂具深度与广度的文化视野。
李延年
资料来源:吉隆坡永春会馆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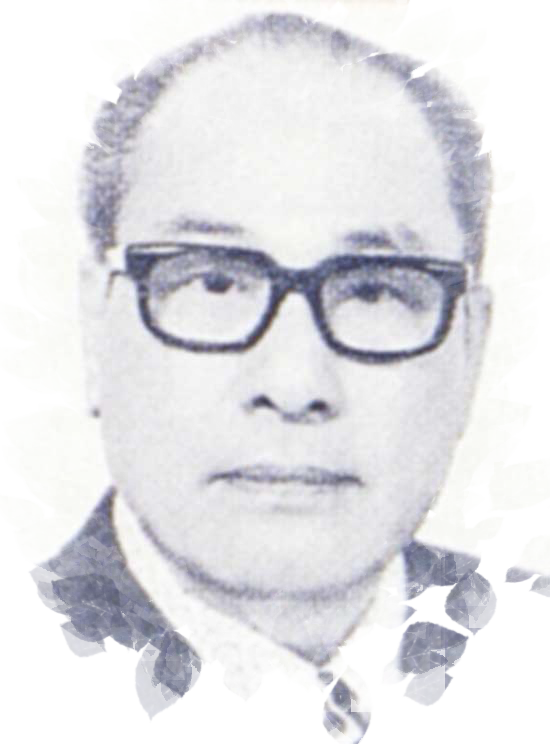
邱祥炽
资料来源:吉隆坡永春会馆提供

邱祥炽任内最大的功绩莫过于引领十五华团将《国家文化备忘录》提呈给政府,以及成功举办华人文化大会,这在当时不但激起了华团推动文化活动的热潮,也因为与全国华团一系列的合作而产生更密切的联系,并且经常针对华社问题而举行联席会议,马来西亚华团史上才因此有了“十五华团”这个最具代表性的华团组织代号的出现。9十五华团即是1990年代林玉静时代催生的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简称堂联)的前身,此一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最高领导组织于1997年才易名为华总。上一任任华总会长方天兴,以及总秘书蔡维衍博士的祖籍地均是福建永春。
邱祥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华团领导人物的代表。除了《国家文化备忘录》之外,在他任内推动成立和草拟的民权委员会、华团宣言、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即华社研究中心的前身),对我国华社产生深远的影响。1993年邱祥炽因长期对华社做出巨大贡献而获颁林连玉精神奖。10
李延年与邱祥炽之后,吉隆坡永春人仍然继续在雪华堂作出贡献。其中担任较重要职务者为在1986年张景良任内曾任副会长的蔡维衍博士。1992年林玉静担任会长时期,黄茂桐担任副会长,尤培胜、陈达真担任董事。1998至2000年,蔡庆文与郑福成同时出任副会长,其中律师出身的蔡庆文担任副会长至2009年,过后才转任法律顾问。雪华堂在上世纪从创会、成长到会务改革,永春人几乎都参与其中。但吉隆坡永春人不仅仅是以吉隆坡永春会馆的代表参与雪华堂的会务,例如李延年、黄茂桐、蔡庆文等更是以雪兰莪福建会馆代表的身份进入雪华堂董事会。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永久董事废除之争议
雪华堂是自1923年成立后的首十年,因大礼堂的命名应采陆佑堂或者中山堂而出现争议。从这件事也可看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吉隆坡华社于在地化和中国化之间出现矛盾。因两派互不退让,结果导致雪华堂领导层严重分裂,财政张郁才甚至因此愤而辞职,筹款委员会的许多成员也呈辞,筹款小组主任三度易人。董事会几次会议因人数不足而流会,会务因此几近陷入瘫痪,导致兴建工程一延再延。
在雪华堂兴建期间,又适逢经济萧条,土产价格滑落,市场不景,募款劝捐成绩与预期目标落差甚大。为免会所兴建之工程因财政困难而停顿,雪华堂再召开第二次华侨大会商对策,议决由吉隆坡各行各会馆出任永久董事来加强雪华堂之力量外,并组织募捐团,发动大规模募捐行动。“永久董事”的名词第一次出现在雪华堂的文献上。11简言之,“永久董事”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而产生的,奠定了雪华堂的社会基础。
1933年10月20日,在中华总商会召开雪华堂受托人会议,会上促请广肇会馆、福建会馆、惠州会馆、广西会馆、潮州会馆、番禺会馆、中山会馆、东安会馆、会甯会馆、三水会馆、福州会馆、永春会馆、茶阳会馆、嘉应会馆、赤溪公馆、琼州会馆、中华总商会、雪州锡矿公会等十八个团体,以及树胶公会委派代表,组成雪华堂第一届董事会。同年11月3日,安溪会馆、最乐剧社和人镜剧社亦加入董事会。1938年12月18日行团也出现在董事会名单之中。
雪华堂的最早二十二个董事,以地缘性会馆和方言群组织为主,基本上包含了福建、广东、客家、潮州、海南、广西及福州七大方言群。同时,各方言群之下的以地缘做为纽带的会馆也均受邀为董事会成员。董事会的组成结构反映出当时吉隆坡华人社会的结构。广东会馆、顺德会馆、高要会馆、冈州会馆、兴安会馆、河婆同乡会、晋江会馆及龙岩会馆并未在二十二个永久董事之列,乃因雪华堂召开受托人会议时,这些会馆还未成立。
雪华堂出现“永久董事”的历史渊源,是因为过去为大礼堂命名出现争议,引发个人董事争相辞职,为恐无人要当董事,在客观需要下才邀请二十二团体列为永久董事。除了十七个会馆组织与三个业缘性组织之外,人镜剧社和最乐剧社之所以在受邀之列,是因为两者先后不遗余力为雪华堂筹募建筑经费。12简言之,二十二个永久董事的出现,是历史情境使然,而不是他们主动去争取在制度上特别设计下所产生的。吉隆坡永春会馆领袖在雪华堂领导层出现堂名之争议而争相辞职导致建筑经费筹措困难期间,仍然肩挑募捐委员会的重任,应是受邀成为永久董事的要因。
“永久董事”课题会被提出,主要源于是雪兰莪和吉隆坡地区华人社会变化所致。随着华裔人口的成长与华人社团组织的增加,雪华堂的会员结构也应当作出调整。 1975年后,在李延年的领航下,雪华堂组织文化开始蜕变,在开放门户政策下,雪华堂的会员从原有的二十二个华团增加到一百九十七个。13雪华堂虽然自此扩大了社会基础,却也因此加剧后来在领导层改选时,应否取消永久董事资格的争议。
1980年,永久董事课题第一次被提出讨论。马来西亚汽车银业公会代表建议永久会员应该开放,不限于二十二个创会团体。雪华堂所有三十九名董事应由永久会员和普通会员选出,以取代原有董事会中二十二个团体自动中选制。当时的执委会同意讨论修改章程提议,虽通过展延至一适当时间再商讨,但随后却被搁置。1983年9月22日,社团注册官批准了《雪华堂章程》第3章第3条(2)和(3),不仅列二十二个董事团体为永久会员,还规定这二十二个团体的代表自动成为董事。14这两条章程条文确立了二十二个永久董事的地位,却也因此激发了要求修改的声浪。
1986年的会员大会上,雪兰莪彭氏联宗会再度提出检讨二十二个永久会员自动成为董事的提案。唯此议案之提呈因不符修改章程程序而未获通过,但雪兰莪彭氏联宗会代表彭谷明提出的另一相关议案却通过了:“本大会授权下一届董事会修改本堂社团及非营利有限公司章程,研究其中有关二十二个永久会员的代表自动成为董事的条例,并另立条例规定所有董事皆由会员大会选出,以符合民主精神。” 同年5月24 日第23届董事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中,成立了九人的修章小组,议决董事会在未进行修改章程之前,必须先征求二十二名永久会员的意见。而且修章小组的任何建议,都必须经过董事会的讨论才决定。这项决议在1987年3月11日即收到了二十二个永久会员(当然董事)中的二十个会员的联名,坚决反对撒消二十二名当然董事的提案。15显然不同阵营董事已于这段期间围绕着永久董事课题互相较劲。
1994年雪华堂领导层进行改选,当时的票选董事有十七位,永久董事二十二位。当权派的吴德芳以一票险胜挑战派的颜清文。挑战派认为票选董事人数少于永久董事是导致他们落败的原因,于是雪华堂再次出现检讨永久董事资格的声音。1998年,颜清文成功接任雪华堂会长,但其在董事会的复选是以一票之险胜刘磐石而当选,再度引发了部份雪华堂会员质疑二十二个永久董事存在的必要性。颜清文出任雪华堂会长期间,郑福成也出任副会长一职。当时吉隆坡永春会馆并不赞同废除二十二个永久董事职位。在特大进行之前,郑福成再次向颜清文表达要保留永久董事的意愿。16与此同时,大部份永久董事也联名致函雪华堂会长颜清文,表达反对取消永久董事资格的意愿。期间也有人提出由二十二名永久董事互选十五名的折衷方案,以减少永久董事名额,增加票选董事人数, 这项建议兼顾到票选董事的影响力,同时亦肯定永久董事的历史贡献。唯此方案得不到大多数董事的认同而最终作罢。
1999年4月26日雪华堂召开特大,以155票对29票通过废除永久董事的建议,雪华堂永久董事自此成为历史名词。唯人镜剧社的代表李善图为保留二十二名永久董事地位不惜入禀法庭,但结果有关申请仍遭法庭驳回。17雪华堂永久董事团体代表之一的雪兰莪华人行团总会会长刘磐石更因此另起炉灶成立吉隆坡华人大会堂,迫使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改名为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简称隆雪华堂,目的是为防堵雪兰莪和吉隆坡的华人事务最高代表机构闹双包,导致雪华堂闹分裂。
雪华堂永久董事虽然在争论十几年后才被废除,但不代表我们能够忽视这二十二个华团在雪华堂建立初期稳住基石的贡献。当初因为堂名争议引发董事争相辞职,为稳定领导层,避免出现雪华堂成立不久即面对无人领导的窘境,才在制度上首创永久董事的职位。这是历史条件促成了永久董事的出现。永久董事的地位并非永恒不变,亦需因应社会环境的变迁、组织成长所引发的变革需求而进行检讨。至于是否该局部保留或全面取消,很多时候是由“人”的因素来决定的,而不是从历史贡献的视角来着手处理。
历史本来就具有多个面向,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立场来看待问题,所得到的答案也不尽相同,当中还存在着领导人个人政治立场与利益牵扯的因素。这当中不需要做出对与错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因果脉络的探究-究竟二十二个永久董事是在什么样的动因之下被提出废除,以及废除之后对吉隆坡华社带来怎样的冲击?产生怎样的历史意义,这些才是我们所应该关注的。
吉隆坡永春会馆与其他雪华堂董事反对取消雪华堂永久董事之声明
资料来源:吉隆坡永春会馆提供
从吉隆坡华社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永春人在主要华团组织占有一席之地位。从雪华堂创建初期,永春人即在筹募小组里担负重任。独立后永春人开始进驻雪隆领导核心。李延年同时在吉隆坡永春会馆、雪兰莪福建会馆、永联会、马来西亚福建联合会、雪隆工商总会、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以及雪华堂担任会长或其他要职。如果说马来西亚华社在1970年代进入李延年时代,实不为过。吉隆坡永春社群核心领导层也在这时期站上大马华社的顶峰。继李延年之后,邱祥炽、林玉静也曾领导雪华堂。林玉静后来亦担任华团最高组织--堂联亦即华总之前身的领导人。
华团组织随着时局的发展亦需调整步伐。雪华堂二十二个永久董事争议许久才落幕,身为永久董事的吉隆坡永春会馆,在争议期间已经表达本身的立场。虽然永久董事资格被废除,但吉隆坡永春会馆并未因此退出雪华堂,显现吉隆坡永春会馆尊重民主的精神。
2005年4月23日吉隆坡永春会馆表达不退出隆雪华堂立场
资料来源:星洲日报

1 《雪森彭鑛务公会120年暨鑛业史》,页14。
2 郑良树等著:《苟利社稷全力以赴—雪华堂与华社风雨同舟八十载》,吉隆坡:雪华堂联络委员会,2002,页5-6。
3 郑良树等著:《苟利社稷全力以赴—雪华堂与华社风雨同舟八十载》,页7。
4 郑良树等著:《苟利社稷全力以赴—雪华堂与华社风雨同舟八十载》,页6。
5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庆祝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77年,页146。
6 所谓执事关联(Interlocking officership)就是指对一或数个社团聘用同一人士为董事、理事
或重要职员的现象。详见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小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台
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0年,页133。
7 郑良树等著:《苟利社稷全力以赴—雪华堂与华社风雨同舟八十载》,页18。
8 郑良树等著:《苟利社稷全力以赴—雪华堂与华社风雨同舟八十载》,页28-30。
9 郑良树等著:《苟利社稷全力以赴—雪华堂与华社风雨同舟八十载》,页29。
10 郑良树等著:《苟利社稷全力以赴—雪华堂与华社风雨同舟八十载》,页30。
11 郑良树等著:《苟利社稷全力以赴—雪华堂与华社风雨同舟八十载》,页203。
12 郑良树等著:《苟利社稷全力以赴—雪华堂与华社风雨同舟八十载》,页201。
13 同注47。
14 郑良树等著:《苟利社稷全力以赴—雪华堂与华社风雨同舟八十载》,页204。
15 郑良树等著:《苟利社稷全力以赴—雪华堂与华社风雨同舟八十载》,页205。
16 丹斯里郑福成口述,1/1/2014于麻坡。
17 郑良树等著:《苟利社稷全力以赴—雪华堂与华社风雨同舟八十载》,页198。